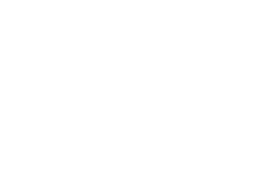Originally By 何燃冬 ✕《莽莽》編輯部 For 莽莽 MANG MANG
Published: 20 Nov 2023
李昱函,曾經是一名為了兒子維權的母親,數年前選擇踏上更加危險的道路:成為一名人權律師。在代理了709鎮壓中的王宇案後,她正在面臨報覆。如今,她已經在看守所里度過了六年,剛剛過完74歲生日。“人民”法院一紙遲來的判決決定了她還要再等待半年時間才能回家。
2017年的初夏,一位人權律師從北京出發,乘坐飛機前往吉林省長春市。看起來,她只是去那里辦一起平常的案子,這讓她並沒有引起當局的警覺。
那時已經六十多歲的李昱函在人權律師的圈子里是一位備受尊敬的“老大姐”。照片里的她梳著松散的卷發,目光堅定地注視著前方,不羈而堅韌。
長春並不是她的目的地。幾天以後,她重新啟程,在到達位於該省西北部邊境的白城後,把交通工具換成出租車,以避開龐大的數字監控系統。一旦她在網絡上購買火車票,國保1將獲知她的行程,並對她展開攔截和騷擾。
烏蘭浩特。這是一座位於內蒙古東部的小城,荒涼而人煙稀少。因為沒有什麽工業,天空總是呈現幹凈而深邃的藍色,鑲嵌著立體的雲。她要去這里和她的一位當事人見面。
兩年前的2015年,中國政府針對人權律師發起了一場震驚中外的鎮壓運動,後來被稱為“709大抓捕”,300余名律師、活動家和他們的家屬受到傳喚、抓捕和酷刑。李昱函的當事人是王宇——另一名著名的人權律師,這場運動的第一位受害者。
2015年7月9日的淩晨,數十名警察包圍了王宇位於北京的住所,將她綁架到她自己至今仍不知位置的秘密拘押地。幾個小時前,她的丈夫和兒子在機場被捕。
失蹤一年多後,王宇出現在了中國官方媒體播出的電視節目上。在一大片綠色草坪的背景里,她穿著白色T恤,坐在舒服的扶手椅上——精心布置的輕松氛圍。“我現在身體非常好。我被羈押期間,我的各項權利都得到了很好的保障。”王宇對著鏡頭說道。
後來我們知道這是一場可恥的強迫電視認罪。人權組織保護衛士2018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揭露了中國政府如何通過“威脅、酷刑和制造恐怖氣氛”來強迫電視認罪。
“‘講述中國的故事’意味著這些對人權的侵犯行為最終會裝扮成‘新聞’的形式, 流向世界各國的屏幕上。”
保護衛士在2018年發布了一份名為《劇本和策劃: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的報告,揭露了709鎮壓中中國政府如何使用強迫電視認罪來對律師實施打壓。
作為交換,在這之後不久,王宇被釋放,但並沒有獲得自由。她被強行送回內蒙古烏蘭浩特,那里是她的家鄉。國保為她租用了一間公寓,強迫她住下,將她軟禁起來。房間對門就住著國保,以便時時刻刻地監視她。“我們走到哪兒,國保都會跟著我們。”王宇說道。
李昱函要去見王宇,這是一個大膽又危險的抉擇。“那里很偏僻,很難到達。”王宇這樣描述她家鄉的那座小城,國保禁止任何人探望她,前來的人被以檢查身份證相威脅。同行的還有文東海,另一位勇敢的人權律師。
為了避開國保的嚴密監視,李昱函把自己隱藏在帽子和墨鏡之下。他們先到達王宇母親的家里躲藏起來。王宇在晚些時候乘坐國保的車來與他們會合,這讓國保以為她只是探望自己的母親。國保們放松了警惕,繼續留在樓下的街道——這是一份輕松的工作,絕大多數時候,他們只需要躺在車里休息,只是有時需要攔截那些貿然來訪的“Persona non grata”(不受歡迎的人),例如人權律師、記者和外交官。
她們擁抱在一起。“大概兩年的時間里,我是和外界完全隔絕的。”王宇開始陷入回憶,講到這里時,她的情緒有了些略微的起伏,“兩年了,第一次見到親人那樣的感覺,非常激動啊。”
精心策劃的“騙局”被揭穿,這激怒了中國政府,當局很快發起報覆:幾個月後,李昱函在沈陽被捕。檢察官指控她涉嫌“尋釁滋事罪”和“詐騙罪”。隨後她被嚴重超期羈押,據稱期間受到酷刑,直到6年後的2023年,也就是最近,才宣判。漫長的歲月里,她的一位代理律師已經離世。
李昱函拒絕認罪,當庭宣布上訴。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他們不可能承認錯案,改判的空間幾乎沒有。”李昱函的律師坦誠,案件的二審“已經不是法律問題”。
中國法院將二審發改率(發回重審和改判率)作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標。法官無法獨立審判,共產黨要求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接受其領導,以確保判決結果符合黨的意志。法院的審判結果被重新推翻被認為是對黨-國體制司法權威的挑戰。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2022年全國法院司法統計公報》,2022年,刑事案件的二審改判率只有9%,這個數字在近年來持續降低。在敏感的政治案件中,上訴幾乎沒有希望。
“但是從理念角度來講,該發出的聲音還是要發出,”李昱函的律師說道。“最起碼要留下一些印記吧。”
自2012年習近平上台以來,共產黨加強了對法治的表述,這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擴大政治自由化的象征。但很快,活動家們發現自己被欺騙了:全國各地法庭的人權律師正在遭受更大力度的鎮壓——在709大抓捕中達到頂峰,至今仍沒有停止的跡象。
李昱函被捕九天後,當習近平在十九大上宣布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時,活動家們已經清楚,對於他們而言,法律是鎮壓工具,無法提供保護。這個由習近平直接領導的小組不受監督且不透明,淩駕在政府和司法機構之上。“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十九大報告中寫道。
“繼續對律師的打壓會變成常態。”
29原則理事潘嘉偉對《莽莽》說。
當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開始停滯,統治出現危機。中國政府正在將法治重新表述為“依法治國”,通過加強民主性缺失的立法來為威權主義政權創造正當性來源。但是,人權律師顯然仍舊固執地將法治理解為法律對權力的約束,他們希望通過為個案實現正義來鞏固公民的權利基礎。
“‘依法治國’只是通過惡法作為人治的手段,”英國人權組織29原則理事潘嘉偉告訴《莽莽》。“中國政府所聲稱的‘建設法治國家’只是維持中共獨裁的做法,絕非民主國家所展現的依法治國和法治精神。”
“709案件有指標性,過了八年後,仍然有像李昱函律師這樣的案件,被關押多年後仍被重判,反映當局對人權律師絕不手軟。”他補充道。
近年,709大抓捕的直接受害者已經相繼出獄,但這場運動並沒有結束。中國政府改變了策略,變得更加隱秘——一次鎮壓一個律師,以防止出現新的受害者家屬的聯結,“709妻子”們聲勢浩大地聲援行動令他們恐懼。包括李昱函在內,一些為709律師辯護的律師正在相繼入獄或失去律師執照。
一個執著的人
1949年,李昱函出生於遼寧撫順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工人,母親沒有工作。和共和國同歲的她年輕時的經歷和時代的潮流緊緊綁定在一起:上中學時因文革爆發而失學的她加入了紅衛兵,曾到北京串聯,到天安門廣場去見毛主席。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伴隨著毛澤東呼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68年,李昱函來到農村插隊,跟著農民插秧、種地。一直到文革結束前兩年,她才回到城里,最初學過赤腳醫生,在衛生所做些臨時工作;等到國家政策允許知青返城,她被正式調回,分配到撫順當地的一個工廠工作。
中國在1977年恢覆了高考,但李昱函沒有選上考試名額,因此並未參加。並不甘心的她在工廠的工作之余報名參加了電視大學來自學。到了八十年代,李昱函和同廠的另一名工人結婚,在1981年生下了兒子,這讓她的學習進程中斷了。
八十年代末期,李昱函重新開始自學法律。“我的母親是非常要強的人,有一種不屈的精神。”李昱函的兒子、目前生活在德國的馬先生接受《莽莽》采訪時說道。他認為母親的這種性格是促使她選擇學習法律的原因。
工廠的工作十分辛勞,李昱函就利用下班的業余時間自學。後來通過參加成人自考,進入吉林大學的法律專業學習。她在1990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並在一年後開始執業。據統計,在這一時期的全國律師人數僅為三萬余人。
平靜的生活在1997年被打破。這一年,李昱函的兒子在中學里遭到嚴重的校園暴力:他被幾個校霸索要錢財和毆打。這導致孩子患上了精神疾病,不敢上學,後來被醫院鑒定為二級精神殘疾。
校霸的父親名叫周長江,是當地的一個房地產開發商老板。李昱函找到他,要求獲得道歉和賠償,但被後者拒絕。當學校和警察因為懼怕周老板的勢力而拒絕處理後,李昱函開始通過法律訴訟為自己的兒子維權。
但這激怒了周長江,他開始對李昱函一家實施報覆。他找來自己的打手騷擾李昱函的兒子,李昱函就帶著兒子搬到沈陽,然而周長江仍舊不放過他們一家。
在多次遭到黑社會毆打後,李昱函的丈夫因懼怕報覆而希望她停止維權,在被她拒絕後選擇了離婚。法院把孩子的撫養權給了父親,但兒子卻繼續跟著李昱函生活,父親在那場下崗潮中失去了工作,無力撫養他。
周長江和他的小弟們永遠陰魂不散。李昱函的兒子考上了大學,仍然繼續被騷擾。為了躲避,他進入軍隊服役,然而周長江又派自己的律師過去,把他曾患有精神疾病的事情告訴了軍隊領導。於是,曾立下三等功的他失去了讀軍校和提幹的機會,只能在兩年後覆員。
他的精神疾病時常因周長江騷擾的刺激覆發,這讓李昱函數年來都奔波在帶他看病、散心的路上。李昱函仍舊堅持控告,周長江的報覆開始變本加厲。
最嚴重的一次,李昱函在司法局大門口被三個打手綁架到汽車上,碰巧遇上一個電視台在拍攝才得以脫身。然而公安局卻放走了綁架者並拒絕立案,檢察院又對她的控告百般刁難。另一次,她在市場被人從背後用鈍器襲擊,肋骨骨折,後腦受傷。周長江的律師公然對她承認這是他們所為,並威脅要把她“打瞎眼睛,然後滅門”。
“再這麽控告,找沒人的地方先打瞎眼睛,然後給你們滅門。”
周長江的律師對李昱函說道。
為了躲避報覆,李昱函只好借錢把兒子送到德國上學。但她卻從未停止維護自己和兒子的權利的步伐。
訴訟拖了很多年,法院換了數任法官都不敢作出判決。周長江公然宣稱他和法院院長、公安局局長“都是哥們”。在終於得到了勝訴結果後,4萬余元賠償也始終得不到執行。李昱函的弟弟李永生告訴《莽莽》,到2017年李昱函已被羈押後,他嘗試幫助他的姐姐執行賠償,但失敗了。
周長江沒有回覆《莽莽》的置評請求。截至發稿時,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的查詢顯示,自2015年開始,周長江共有11個失信被執行記錄。但遼寧建設工程信息網公開的一份中標公示信息顯示,2017年,以周長江為項目負責人的公司獲得了沈陽市的一個公安局派出所維修改造工程的施工資格。
奔走一年多終“會見”
李昱函在遼寧堅持不懈地控告當地政府的非法和不作為,這讓她的律師工作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以至於無法繼續在遼寧執業。不得已,2009年,她轉到北京的一家律所工作。文東海律師在他一篇回憶李昱函的文章中開玩笑地說道,在北京堅持繼續上訪的她變成了“律師訪民”。
接下來的幾年里,因為繼續上訪,遼寧公安數次到北京來對她施加迫害:當街毆打,或是抓入駐京辦的黑監獄2。即使心臟病發作,她也無法得到治療,警察甚至會繼續對她使用酷刑。
當李昱函來到北京時,中國正在進入“維權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發的茉莉花革命蔓延到中國,廣州等城市爆發反政府的和平示威。人們對未來充滿希望。大約這個時候,本是為自己和孩子維權的李昱函,加入了人權律師的行列中,開始接手所謂的“敏感案件”。
“一些是信仰方面的案子,”王宇回憶道,她指的是法輪功案。李昱函的另一些當事人還包括被迫害的退伍軍人和各地訪民。
當2015年7月席卷全國的鎮壓來臨時,李昱函並沒有直接成為當局的目標,直到她在一個月後勇敢地代理被捕律師王宇的案件時才卷入其中。王宇是那場運動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她和丈夫包龍軍、兒子包卓軒都遭遇強迫失蹤。
7月9日淩晨,數十名警察包圍了王宇位於北京的家。水、電和網絡被切斷後,警察破門而入,把王宇套上黑色頭套,帶到一個秘密的拘留地點——她至今仍不知道在哪。
此時她的兒子包卓軒正在父親的陪同下前往機場,如果一切順利,他將在澳洲開啟留學的新生活。在登機口,他們被攔下帶走,隨後一同失蹤。一份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3的統計數據顯示,接下來的四天里,在全國範圍內有114名律師和維權人士被帶走、傳喚或約談。
整個抓捕的過程里,王宇甚至沒有得到一份正式的法律文書。她向審訊警察抗議整個行動就像一場“土匪綁架”,拒絕回答審問。隨後,她開始受到酷刑。
“我告訴你,你別以為不抓你,你就以為你沒事兒了。不抓你則已,要是抓你就讓你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負責審訊王宇的預審警官對王宇這樣說道。
王宇在《失蹤人民共和國》中講述了這段經歷,這本書已於2017年在美國出版。關押她的房間里掛著厚重的窗簾,沒有一點陽光。辦案人員在連續一周時間里對她剝奪睡眠,並給她帶上沈重的手銬腳鐐作為懲罰。每一天,她都被強迫在監控前脫光衣服接受檢查,她認為這是對女性極大的侮辱。
幾天後,王宇工作的鋒銳律師事務所主任周世鋒在央視上認罪,並攻擊她“二楞子,胡整”。辦案人員向王宇播放了錄像,她仍舊不為所動。當警察強迫她電視認罪時,她激烈地抗拒,以跳樓相威脅。
王宇開始要求為自己委托律師,當她報上一些律師的姓名時,警察告訴她他們將把這些人全部抓捕。後來,連審訊警官都看不下去了,勸她說,“你別害別人了,你要是說誰就抓誰”。當警察欺騙王宇“你現在被抓了沒人管你”的同時,她的數十位律師同伴受到恐嚇,被禁止代理她的案件。幾個已經著手代理的律師迅速在巨大的壓力下被迫退出。
在這樣的嚴峻局勢下,李昱函毅然選擇了接下這個案子。我們並不知道,此時的她是否會意識到,這將為她帶來六年多的牢獄之災。
但是作為人權律師,李昱函感到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沒有人代理這個案子,那誰來代呢?那可能就沒有人代。”王宇回憶起李昱函的堅持。
王宇補充說,人權律師對此想法一致。
“他(文東海)說當時在火車上就有人給他打電話。就問他說,王宇的案子你還敢代啊?他說,那怎麽辦呢,那我也害怕呀。”
因代理王宇案,李昱函律師和文東海律師面臨極大的心理壓力。王宇根據自己的回憶描述了文東海剛剛接手該案時的情形。
三天後的早晨,包卓軒被釋放,隨即被家人接到天津的爺爺家居住。他翻出了父親留下的電話簿,開始按順序給上面的律師們打電話,為父母尋找救援。他曾在機場被帶走時激烈反抗,記下了一個警察的警號,現在,他把這串數字重新背誦出來,這對夫婦的律師朋友據此推斷出抓捕王宇和其他律師的警察來自天津市河西區。
在發現包卓軒正在和律師取得聯系後,國保將他送到烏蘭浩特。隨後,他在一次失敗的偷渡行動後被置於更嚴密的監視之下。
在接下來的一年里,李昱函開始頻繁地往來於京津兩地。她數十次來到天津市的公安局和看守所里要求會見,但是,王宇被化名關押,她無法查詢到王宇的名字。
一次,李昱函和其他幾位709鎮壓受害者的律師、家屬一起去天津的看守所申請會見。李文足和王峭嶺都帶著自己的孩子,孩子們就在看守所的接待室里到處亂跑。李昱函問警察,為什麽律師三證齊全4就是不能會見,警察則搪塞說要請示領導。又過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是午飯時間,警察繼續找拙劣的借口,說領導開會去了——領導的會開不完。
有人說:“領導也得吃飯,咱們等領導!”他們買了飯,就在接待室里吃完。等到下午兩點半,警察又說“領導不來了”,由於家屬需要帶著孩子開車回北京,大家只能離開。
李昱函還毫不畏懼地向當局的違法發起挑戰,在一份提交給天津市和平區檢察院的申訴材料中,她要求追究中央電視台等播放王宇認罪視頻的媒體的法律責任。
即使無法會見王宇,李昱函仍希望去拜訪她的母親和兒子,給家屬一些精神支持,但國保總是從中作梗。2015年10月23日,包龍軍、包卓軒獲得天恩國際交流基金會頒發的希望獎,李昱函想要把這個消息告訴王宇的母親和兒子,就動身前往烏蘭浩特。但就在那天早晨,警察突然把王宇的母親接到派出所,並沒有什麽正事,只是和她閒聊。警察很客氣地給她沏茶倒水,還端來了水果,直到很晚才送她回家。後來,老人才知道,那天李昱函來探望她。
得知王宇的母親被警察帶走後,李昱函又追到公安局。她沖進里公安局大樓里,一邊上樓梯一邊喊“蒙蒙(包卓軒)得獎了”,最終被警察推搡著趕了出去。
2016年年初,當王宇被轉送到天津的看守所里,她感覺環境正在變得輕松——警察已經不再提審她,而是每天把她請到管教辦公室談話。警察繼續要求她電視認罪,並以她在國內的兒子相威脅,為了換取把兒子送出中國和丈夫的釋放,她在經歷了無數個不眠之夜後妥協了。52018年,包卓軒在原本計劃出國的三年後終於踏上了澳洲的土地,接著又輾轉來到美國,接受《莽莽》的采訪時,他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一所社區大學攻讀社會學學士學位。
王宇在2016年7月23號取保候審,又在天津滯留了一段時間後,一家人一起回到烏蘭浩特,住進了國保安排的房子。她的一舉一動都被嚴密監視:一旦踏出家門,國保設在附近的辦公室就會警鈴大響;即使只是出門買點蔬菜,便衣警察也尾隨其後。
半年多後,當李昱函終於和王宇取得聯系,她立刻踏上了“會見”的旅程。在王宇被關押的一年多的時間里,她未能成功會見哪怕一次。王宇甚至對李昱函是自己的律師完全不知。
她們擁抱,訴說著兩年來的無限感慨。只是此時國保還在樓下,他們很緊張,沒有太多的時間敘舊。李昱函繼續做起了律師的本職工作,她讓王宇和包龍軍重新簽署了一些委托書,確認代理關系——她擔心這對夫妻會在取保期滿後再次被捕。然而不久後,需要被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卻變成了她自己。
漫長羈押後仍堅拒認罪
當警察發現李昱函居然突破了嚴密封鎖、如此大膽地挑釁他們的權威時,他們氣急敗壞地將她抓捕。2017年10月9日,這天是李昱函68歲的生日,警察以“融冰行動”為幌子,欺騙她稱要解決她多年來上訪的訴求,當她按約出現在公安局後,至今沒有再走出來。
弟弟李永生在這天接到了李昱函打來的電話。李昱函躲在廁所里,急促地說,警察要把自己刑拘,請李永生向她的同事們傳遞消息。這時,警察已經發現了異常並開始敲門。電話在兩分鐘後掛斷了。
這次被捕以前,李昱函每周都會和在德國的兒子通話聊聊近況,只是她幾乎不會和兒子講起自己接手人權案子的事情。她的兒子表示,他沒有在和母親的最後幾次通話中感到任何異常。
由於正值十九大維穩時期,李昱函的律師朋友們對此並沒有特別地重視,以為她會在十九大結束後被釋放。直到她被以涉嫌“尋釁滋事罪”為由刑事拘留,幾位律師的數次會見嘗試都被拒絕,他們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大約兩周後,兩位律師在看守所會見了李昱函。根據其中一位律師藺其磊的回憶,李昱函告訴她自己受到虐待:她被警察粗暴地推進監區的大門,以至於差點摔倒;被捕以來,她沒有正常的飲食和睡眠,並且無法得到長期服用的藥物。前來和律師見面的時候,她需要在同監室友的攙扶下行走。
12月李柏光律師在另一次會見後發布的通報里描述了李昱函遭受酷刑的更多細節:在冬天,她被要求用冰冷的涼水洗澡,她購買的水果被故意放在廁所淋上尿液。兩個多月後,李柏光律師因一場離奇的肝病而去世。
“我真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們了,我真擔心會被他們迫害死掉!”
李昱函在被會見時對李柏光律師說道。
85名律師和人權捍衛者聯署的一封公開信寄往沈陽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這份信的內容由王宇撰寫,呼籲停止虐待和立即釋放李昱函律師。當國保找到王宇時,她毫不猶豫地承認。“她是我的律師!”王宇激動地對國保說道。《莽莽》檢查了這份公開信的聯署人名單,發現其中已有至少20名律師被剝奪執業資格6,一些人入獄或流亡。
李昱函的羈押被各級法院數次延長,但她從未收到任何正式的批準文書。到宣判時,她已經被超期羈押了六年之久。先後有十幾名律師代理過她的案件。
到後來,案件已不繼續偵辦,法官來到看守所提訊她時,只是讓她認罪。“認罪了就可以出去,”提訊的法官對她說,“你認罪了,我們就好處理了。這些不是我們所能做主的”。
在藺其磊看來,李昱函清楚公權力的欺騙本質。作為一個曾經的人權律師,她已經目睹了太多當局肆意違法的情形。她正是因為在辦案過程中堅持律師的職業道德,依法捍衛當事人的權利,因而冒犯政府,才遭受此般迫害。如今法庭逼迫她認罪,她不能違悖自己的良心。
“稍微有點法律常識、生活常識的人,(都會認為)我不構成犯罪。” 她告訴律師。漫長的羈押已經摧殘了她的身體。
“但她的精神一直沒垮。”律師說道。
該案在2021年初次開庭。起訴書里,她為殘疾的兒子申請低保屬於“詐騙”;在天安門前路過,則構成“尋釁滋事”。律師做無罪辯護,否認了全部指控,稱這是“對公民自由權利的粗暴踐踏”。
這次庭審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最終卻沒有作出判決。律師也無法回答原因,只是說,這種做法“違反道義,踐踏人性”,他們將繼續追究當局程序嚴重違法。
2023年10月25日,李昱函案再次開庭。她在兩名法警的攙扶下出庭受審,如今身患多疾卻長期得不到治療的她,沒有拐杖已無法自己行走。
李昱函當庭提出管轄權異議,她連續二十余年控告沈陽市和平區的法院違法,如今卻由這個法院來審判她。被拒絕後,她起身準備罷庭,在弟弟李永生的勸說下才沒有離開。“他們違法,也把這違法程序走完。”李永生這樣勸說他的姐姐。
律師稱法院甚至禁止他們攜帶水杯,上廁所時都有法警跟隨。但同時,律師表示,法庭“認真聽取了李昱函的自辯,以及辯護人的發言”。
“(我)不認罪,這是打擊報覆。”
李昱函在最後陳述中說道。
王宇也來到了法院,但她被拒之門外,禁止旁聽。她說現場有至少幾十個便衣國保,猶如戒嚴。不過,當各國的外交官員出現在現場時,國保們在一瞬間消失了。
李永生本想在法院門口等等王宇和另外幾個想來旁聽的朋友,但法警警告他不得停留。當他告訴法警自己是被法官請來旁聽時,法警“連勸帶拽”,強行把他拉入院里。在法庭的窗內,他望見王宇已經到達法院外的街道。
旁聽席坐滿了,只不過除了李永生外,全都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李昱函的表妹被攔在法院之外的寒風里。
李昱函被當庭判處6年6個月有期徒刑。人權律師將這種判決譏諷為“實報實銷”,意為政治犯被判處的刑期剛好高於超期羈押的時間。
法院采信了檢察院的所有指控,將李昱函和律師的辯護全部駁回。判決書認定的犯罪事實包括她的“非正常信訪”和為兒子領取低保補助金。不過,庭審結束後,審判長對律師說:“你今天的辯護效果很好,我們都要向你學習。”
沈陽市和平區人民法院沒有回覆《莽莽》的置評請求。判決書並未公開7,《莽莽》得到了一份判決書的副本。
獻給709律師,和律師的律師,和律師的律師的律師…… █
《莽莽》是如何報道這個故事的?
這篇報道是基於對8位在過去數十年里和李昱函有關聯的對象的采訪而寫作的,受訪者包括李昱函的家人、朋友、被代理人和律師。其中一些人因懼怕中國政府的報覆而要求匿名,一名受訪者稱他已經收到多個政府部門的警告,正在承受極大的壓力。除此之外,《莽莽》還閱讀了一些關於李昱函的書面材料,包括公開信、律師的申訴材料和法庭文件。